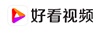此次我想分享的主题是经济增长的非连续性,即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过程只有13个国家跳过去,这说明在经济增长中这是非常麻烦的阶段。工业化促进经济加速发展,可是为什么一到中等收入阶段这种效率就消失?这就体现经济增长的不连续性,它的特征之一就是经济结构在中高收入阶段进入了服务化。服务业的特征跟工业化不能相提并论,它没有所谓工业化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规模收益递增性,其效率改进远低于工业化对整体经济的效率改进过程,经济结构服务化以后,任何国家都会出现结构性减速特征,中国2014年服务业开始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服务业已经占了51%,处在中等服务收入阶段,所以经济减速是有客观原因的。而我们这里讨论非连续性还要涉及更为深刻的东西,人类的思维是归纳法,如果事物是连续的,以前的研究可以用于未来,而非连续性则表明以前的经验未必能用于未来,所以过去中国政府通过政府干预大量资源堆积在工业化部门,导致规模效率递增、中国经济赶超这一个现象在服务阶段,或者说在中等收入阶段变得存在不确定性。
第一个不确定性:整体技术放缓。中国赶超时期的最重要的技术进步方式叫做引进设备式的“干中学”,而这对于资本深化是具有同步效应的,这也导致了中国较高的赶超速度。但是在服务阶段,“干中学”能否导致前沿技术创新变为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并不是说受教育的人口足够多,专利发明够多就一定会转向创新。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是教育年限应超过12年,在这个门槛之前其导致创新的能力是很差的,但是在门槛之后教育能否导致前沿创新亦就是不确定的,它需要市场的一整套激励,这套激励包含了垄断租金定价,比如创新是不是能够得到持续的垄断租金定价,能不能得到更好的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得到资本市场的贴现激励。另外,人力资源投入想变成一个非常有商业前景的前沿创新也是不确定性的,它需要一组制度才能够激励这种创新的完成。当前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TFP增长速度在下降,贡献也在下降,这说明我国整体技术创新速度的下降,但是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也仍是不确定的。
第二个不确定性:服务业发展可能导致城市病,并很容易对制造业产生断裂式影响。广义来看,服务业是跟城市化高度相关联的,城市化的上升是服务业上升,服务业病会传染到工业,因为高成本的城市化会提高土地价格,这种城市化病会加速制造业的断裂。所以高服务业中泡沫病还是小病,如果染到了整个城市化的高成本病,一定对制造业的技术演进和产业升级具有断裂性的影响。如果处理不好,产业升级在制造业中将会加速去工业的步伐,这是因为技术演进跟不上,效率上不来,工业演进中高效率也难以实现,所以在城市化中还可能出现工业升级困难。另外,服务业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拉美国家服务业比重接近甚至超过欧美国家服务业比重,但其效率极其低下,所以服务业如果迈入不了现代服务业,效率不但很难提高,还只能变为人口漂移的蓄水池,服务业比重不是越高越好,而是看其是不是人力资本密集和效率可提升的。所以城市化的崛起,服务业的崛起,如果做不好,会导致制造业断裂,服务业变成人口漂移之地,而不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的发展,更不会导致一个创新过程。
第三个不确定性:在全球技术进步中总是被中国忽视的消费。中国讲到消费都是被动的吃喝玩乐,但其实消费升级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为吃、喝的品质更好,更表现为知识消费的比重在不断提高,广义人力资本的消费比重在不断提高,使得人的素质不断提高,这才有了透过消费导致动态技术补偿,即人的素质不断提高以后,下一代才会有更大的创新性,这是提高要素品质的根本。在中国这方面消费是由最被管制的部门提供,科教文卫体全部是事业单位,这种消费并不能够按市场进行供给,所以我们在消费升级、服务升级中都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卡口,即最需要的提升广义人力资本消费的部分是被管制的。
因为以上的不确定性,技术进步并不能够自动由“干中学”转向自主创新,产业结构由于城市病可能会导致升级断裂,人力要素的动态补偿在消费方面无法得到,这三个问题使我们困惑中国经济是不是能够透过原有模式自动转型?我们觉得非常困难。这三个问题都直指了中国的供给侧体制改革。首先,消费科教文卫体是不是应该进行更强的市场化改革?当然这里有难度,因为它有公共服务性,但是如果不能在这方面改革,现代服务体系和消费难以升级。其次,产业现在依赖于土地、财政的城市化,依赖于行政等级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对整体的服务业和制造业都是断裂式的。最后,在出台拜杜法案之前,美国的科技转换率也就5%,出台三年后,其科技转换率达到55%,所以一个基于法律保护、基于资本市场激励、基于允许一定的租金定价的市场诱惑的一系列制度变革,才能够激励技术创新,使得人的素质提高,才有可能转型升级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